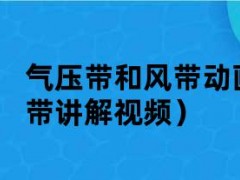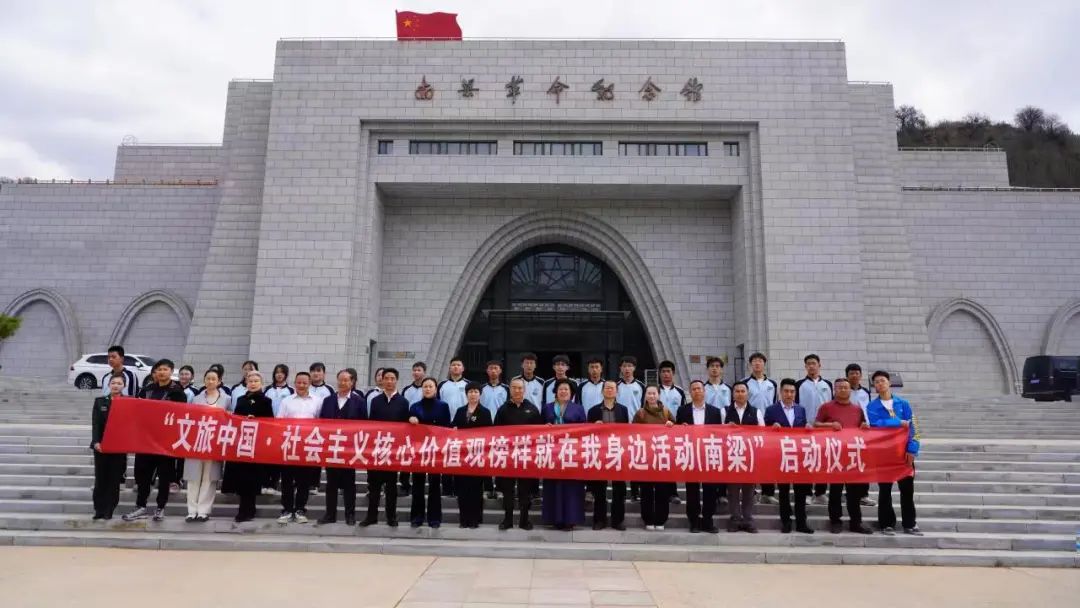利维坦按:
对汗青的探寻是件极其浪漫的事情。我们既能在这一过程中感触到融入群体的归属感,又能找到生从何来的陈迹——前者可以排遣个别作为自力存在而发生的、空间上的伶仃感触,消解界线;后者可以付与当下生活某种时间合理化的注释,这会让人收获安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汗青有着诸多的不确定性,且这些不确定性或许永远也无法解决,但不确定性即或者性,或者性又是另一种意义。

汗青是谬误的鸠合。文物是汗青的客观。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为“通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书《史记》,二十四史里它排第一。这部鲁迅口中的“史家绝唱”,记载了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到汉武帝时期长达2500多年的汗青。现在我们对于这一时期——尤其是上古传说时期的认知,很大水平上依靠于此。
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一书诏令,六国史书尽数焚为灰烬,落入氤氲的汗青暗河中再无踪迹可循,这也是为什么《史记》中记载的上古史料会如斯珍贵——汗青丢了劈头,《史记》则把劈头从新挖出来粘归去,我们才能知道上古所发生的事。
然而,西晋时期(公元279年)发生在河南的一次盗墓运动,让《史记》的正确性遭到了严重质疑。
盗墓者名为禁绝(古音同“否标”),是个职业盗墓人,在其时的都城洛阳一带颇有名气。被盗的墓葬属于战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国君魏襄王,魏襄王身后在棺材里平静地躺了五百多年,直到那天盗墓贼禁绝不请自来。
然则禁绝的此次盗墓,却带出了古代独一留存的、未受秦火虐待的纪年体史书,《竹书编年》。这本魏国史官所著写的官方史书,比《史记》早了足足两百多年。恰是因为被魏襄王带到了墓里,《竹书编年》才能重见天日、留存至今。
然而,书里所记载的上古史与《史记》截然相反,令人瞠目结舌。
《竹书编年》原名《汲冢编年》,经五代战乱散佚,后人从新整顿而得,是以其真实性同样有待商榷。
举个例子。《史记》中记载有尧、舜的禅让美谈:传说中的这两位上古君主都是英明之人,老了之后没有把帝位传给本身的亲儿子,而是自动禅让给了有本事的晚辈,由此被奉为明君。
然则《竹书编年》不是如许写的。书中明确记载:
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
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
意思是,尧帝老了之后被舜关在了平阳,舜由此篡位取得王权。美谈酿成了血淋淋的见笑。
考古讲究“孤证不立”,单一本《竹书编年》也不足以被看成客观事实看待——然而,这段汗青在同为战国时期著作的《韩非子·说疑》中也获得了印证:
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
此四王者,人臣弑君者也。
再来看看先秦时期的《山海经》里是怎么说的:
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
丹朱是尧的亲儿子,若是尧昔时是把帝位直接禅让给了舜,《山海经》又为什么在写到丹朱时还加一个“帝”的称呼?是以有学者猜测,尧先是将帝位传给儿子丹朱,而舜则是动员了政变,从丹朱手中争取了政权。不光如斯,还把本身和丹朱葬在山的两面,死都不跟他葬到一块。
也难怪三国时候的曹丕在强制汉献帝把皇位“禅让”给本身后,说出如许一句大实话:
尧舜之事,吾知之矣。
还有关于伊尹的事。《史记》中记载,商朝的建国宰相伊尹辅佐商王太甲治理国度,因为受不了太甲的玩忽职守与任性妄为,把他关在了桐宫反省,一关就是七年。七年之后太甲洗心革面,伊尹就把他接出来,持续辅佐他做皇帝,是一代贤臣的范例。
除了被视作忠臣,伊尹还被后人称为“烹饪之圣“,是厨师的祖师爷。
然则《竹书编年》里对于伊尹的生平又有另一版说法:
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
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
也就是说,伊尹打发走太甲之后自立为王,太甲经由七年的吃力吃力挣扎,终于跑出来杀死伊尹,这才夺回帝位。哪来的千古贤臣,不外是篡位失败丢了人命的逆臣。
《竹书编年》中所记载的史料,与《史记》相悖之处还有好多,既是史学家研究的重点,又是他们的一块芥蒂。只可惜对汗青的研究嚼烂了说破了,到头来也只能是门概率学——支撑一种见解的文物越多,证据越足,这种见解就越靠谱。
从这个角度来说,发生在当下的时期永远只能留在当下,所谓汗青,只是多数人的一面之词。《史记》,真的只能是“一家之言”。
前人若何考古
我们对一段汗青的还原,只能基于那段时期留存下来的信息。器物也好,文字也罢,都是我们从何而来的证实。
我们的老祖宗显然也懂这个事理,是以很早就起头正视起文物的研究工作。《竹书编年》在战国时期入葬,一向到西晋重见天日,整整隔了五百多年。得亏西晋王召集了其时的多量史官静心研读,才从中识别出竹简所用的战国文字,整顿成册,以飨后人。
而在西晋之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东周,也曾在首都洛阳设立“守藏室”,保管留存下来的玉石丹青等重器至宝,既是大仓库,又是国内最早的“博物馆”。老子李耳在骑着大青牛出关之前,还在这个仓库里当过治理员。
西汉亦是如斯。其时有个异人李少君,传说能驱鬼神,种谷得金,还懂长生不老之术,深受汉武帝赏识。凭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其时有一老旧的青铜物件,便问少君认不认得。少君答曰:这玩意在齐桓公十年那会儿,是摆在柏寝台上的。一看物件的铭文,还真是如斯。
柏寝台原称路寝,是齐侯的行宫。相传台上曾经殿宇壮观,松柏葱翠,现在却只能看到个六米高的大土堆。
少君多大本事早已弗成考,究竟他和汉武帝都没能活到如今,但至少解说早在汉朝祖辈们就把握了必然的文物判定手艺。
往后,南北朝的梁元帝还曾让人收录了一多量古早的碑刻文字,共100卷,编录成册《碑集》。唐人也曾发现过秦国的刻石,十块鼓形的石头上各刻有四言诗一首,内容关于秦国国君的一次游猎,是现存年月最早的石刻文字,至今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中。
秦石鼓上的铭文。
唐代甚至还有划定“若得古器,形制异而不送官者”是要受科罚的,而盗墓者则以贼盗论处。可见对文物的珍爱早在唐代就成了国度法制的主要构成部门。
然则古代考古学的第一个成长热潮,其实是在宋代。
凭据清末《金石学录》的统计,宋代能够称得上是古器物学家的学者已达61人。所谓“金石学”,“金”指金属器物,“石”指石刻碑文,是考古学的前身。盖因其时出土的文物大多为金器、玉器和石碑,尽量有纸帛竹简类型的发现也难以辨识和留存。
很可惜,凭据《宋代金石遗书目》统计,已知由宋人所著、现已失传的古器物学著作多达89部,而在存留下来的30部中,最早的就是《考古图》。
《考古图》共有十卷,收录了从商代到汉代共224件青铜器,1件石器,13件玉器。每一件器物都既有摹画在纸上的器物图样,又有时间、所在、尺寸、撒布经由与收藏概况等具体记录,由北宋学者吕大临在1092年编著而成,称得上是我国传统古器物学正儿八经的劈头。
《考古图》内页。
《考古图》面世没过几年,又有学者王黻受朝廷之命编写的《博古图》问世,扩充之后的《博古图》收录了839件古器物,蔚为大观。
宋代的金石学家有多厉害?他们早早就对《史记》里所记载的汗青有过猜忌。好比宋代的欧阳修连系古碑文、《后汉书》等史料,曾断言史书对于汉魏禅让的具体时间记载有误(详见《辑古录》);赵明诚经由对秦代石刻的仔细精细,发现了《史记》的多处谬误(详见《秦泰山石碑考》)。
再往后,从北方踏来的铁骑把北宋政权赶到了南方,最后奉上了西方,连皇帝都被逼得跳下海里。宋亡之后的元代,学术研究不似往昔这般闹热,金石学也逐渐陷入了低谷。元后的明代固然有些起色,但也就那么一回事,金石人人寥若晨星,很难再谈得上什么提高。
一向到了清代,金石学才真正有了答复的迹象。
光绪年间,国子监里有个大臣名叫王懿荣。王大人生于官宦世家,博学广识。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时候患上了疟疾,便差人到菜市口的一家药店买回一剂中药预备熬起,却在无意间发现:个中一味叫做龙骨的药材上,刻着一些新鲜的符号。
中医所说的龙骨天然不是真的龙骨头,而是泛指远古动物的骨骼化石。王大人常日喜欢研究金石,认定这些符号是比春秋大篆更为古早的一种字体,是以那些甲骨很有或者是殷商遗物,于是起头以每片甲骨二两银的重金,私下收购这些刻有古文字的骨片,第二年便收集了1500多个骨片。
然则这一年,庚子事变爆发,王大人在与八国联军的匹敌中战败,留下一句“吾义弗成苟生”便服毒求死,没死成,又投井,终亡,死后空留下那些没来得及研究的上古骨片。最终是他的生前石友刘鹗将这些甲骨编印出书,著录成书《铁云藏龟》。
而后又有王国维、罗振玉等学究大拿经由几番探寻,终于发现了这些甲骨的出处——河南安阳小屯村。此地在三千多年前曾是商朝的首都,名为殷墟,不光出土了15万枚甲骨片,后来还挖出国宝后母戊风雅鼎(或称司母戊鼎)。甲骨学由此敏捷鼓起。
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片。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王大人投井殉国的统一年,一个住在距离北国都两千公里开外的甘肃窑洞里的道士,也有了重大发现。
这位道士本是湖北麻城人,早年间参过清军,后来逃荒到了甘肃便假寓下来,靠香火钱和摘抄经文为生。在一天的平常清扫中,道长和他的助手无意间在黄沙袒护的洞壁上发现了一扇老旧的小木门。
排闼而入,见得一间七平米见方的狭小洞窟,里头堆满了数千年无人翻阅的五万多件唐经、绢画、文书与各类释教法器,令人叹为观止。
道长名叫王圆箓,王道长住的处所叫莫高窟,而谁人清扫中发现的洞窟,就是后人耳熟能详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法国汉学家、探险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在藏经洞内,这也是藏经洞留下的第一张照片。
和甲骨文的发现一般,藏经洞的发现同样是近代考古史上的重大事件,被视作中国考古学降生的前兆。在此之后,考古学在中国这片“伟大而孤立”的边境上才正式起头生长。
是文物,总会坏掉的
考古学是关于文物的学科,更是关于汗青的学科。但可惜,再美的文物也挡不住时光侵蚀。我国现已建成的博物馆已有5000余处,藏品数高达3700多万件——然而尽量现在的文物珍爱手艺远超前人,也只能尽或者地让文物连结原状。是以,为了珍爱出土文物的平安,我国从2002年起头一共禁止了195件文物出国(境)展览,放几例供赏:
——曾侯乙青铜尊盘

曾是国名,侯是身份,乙是此物件生前所有者的人名,尊与盘各指代一个部门,合二为一。整套物件装饰有龙84条,蟠魑80条,龙蛇蟠动,摄人心魄。多层装饰镂空且互不相连,内层依靠铜梗分层联络,精巧绝伦,是无可争议的中国古代青铜锻造工艺巅峰。
然而凭据史料的记载,这套尊盘是曾侯乙的先祖留下来的,尽量是在他谁人时代,关于这件尊宝的建造工艺也早已失传。人们对于它的建造工艺,至今都只能猜测。
——《刊谬补缺切韵》
《切韵》是一本隋代的韵书,最令人惊艳的无疑是它奇特的装帧技法——各页纸张依序相错约1厘米的距离粘裱,睁开时书页如龙鳞一样互相聚积,是以得名“龙鳞装”。大清亡时,末代皇帝溥仪将其从故宫带出,后流落民间。一向到1947年才被故宫博物院从新购回。
——三星堆青铜神树

这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文物通高约4米,树分九枝,每根树枝上都立着一只神鸟;骨干上逶迤着一条铜龙,有着难以名状的诡谲之感。学术界认为,这颗铜树是古蜀先民祭奠所用,先民们认为此物可通灵、通神、通天。
——《千里山河图》

《千里山河图》的神秘之处,很大水平上在于其作者王希孟。此人只曾在汗青的切片中被说起只言片语,尽量是作品也只有这么一件留存于世。在这十余米的绢本上,画与作者在精神上几近成为一体,隐密了来路和归途——孤卷已成千古,一瞥就是惊鸿。
可惜的是,承载《千里山河图》的蚕丝纤维极其脆落,作画所用的矿质颜料又非常厚重,每次睁开与关合都邑伤害画作,是以文物局才将这幅画归于不常展出的文物一波,2017年的展出一时间也成了热点事件。
其实不止是《千里山河图》,每一件文物都处在迟缓的熵增过程中,只或者越来越接近灰尘,再也没有或者恢复如初。国度文物局发布的195件禁出文物中,像《千里山河图》如许不设常展的还有40件,此外更有26件属于不公开展出的领域,其珍贵性可见一斑。
然则这里存在一个对立逻辑——限制展出是为了更好地珍爱,而珍爱的目的又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若何才能经由手艺实现非损坏性的文化流传,既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至宝,又能让他们获得最好的珍爱,将在很漫长的将来里成为一个待解决项。
其实早在客岁7月,vivo影像实验室就成功挑战了一项高难度义务:用vivo X50 Pro+手机的超高清夜拍功能,拍摄出传世之作《千里山河图》。
壮大的9亿像素全景拍摄,尽量是在幽的情况中也能尽数拍下瑰丽的山水江河,每一处细节都清楚可见。
为助力实现这一方针,vivo在本年一月提议了「数字国宝助力规划」,进展经由科技立异来匡助流传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可以拍摄美,赏识美,拥有美。
比拟于累手费神的专业相机械材,手机无疑更适合顺手快拍,vivo X系列壮大的暗光高清拍摄能力,将助力每个使用者抓住美的瞬间。
就在上个月,vivo又一次走进三星堆博物馆。用vivo X60 Pro+壮大的「科技灵眸」之力,拍摄下一件件穿越古今的三星堆文物,匡助文物的数字化归档留存,使得数千年的汗青也能在数字世界中熠熠生辉——尽量是无法身临其境的你,也能够经由vivo的镜首级略到古文物那令人赞叹的艳丽。
(点开上方短视频,走进vivo三星堆博物馆拍摄之夜)

人文之悦,既是对汗青的赏识,又是对当下的感知。vivo始终进展可以经由科技的立异力量,更好地办事于用户。从Hi-Fi到屏幕指纹,到周全屏,再到微云台,手艺能让你随时随地记录下人文的美,分享出欣喜与温情。

在vivo看来,影像是人文价格的最佳施展。作为vivo的新一代专业影像旗舰,vivo X60 Pro+有着几近无可抉剔的壮大影像机能,后置镜头模组中所包含的一枚潜望式超远摄镜头和一枚50mm专业人像镜头,由vivo结合蔡司研发而成,可以显著增加拍摄能力。
最值得注重的是,后置镜头模组中所包含的一枚高达5000万像素的GN1超感光主摄镜头,与一枚4800万像素的超广角微云台主摄相得益彰,配合搭建出vivo X60 Pro+奇特的双主摄影像系统。尽量是在幽的博物馆中,也能匡助用户随意捕获文物的细枝小节。

不光如斯,vivo X60 Pro+的黑光夜视2.0算法会在极暗的拍摄情况中主动开启,“软硬兼施”的壮大手艺内核能显著提拔影像质感,让大美无须再躲藏在阴郁之中。
立异,只为存眷你所关心的一切。
文/王举
本文由王举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概念,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